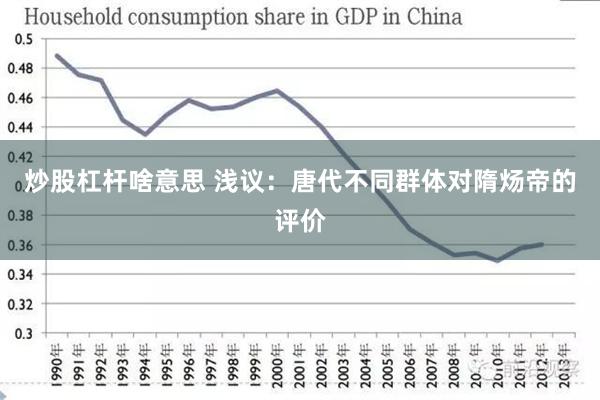
隋炀帝是千古有名的暴君,然而,如果全面看待他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后人都不得不承认他还是为后世留下一些遗泽,
近如与突厥、高丽等政权、民族的关系、唐初的政治格局,远如鼎鼎有名的大运河等,都可算作他的功业。
因而对于后世人来说,如何评价隋炀帝,就成为一个颇为考验史识的题目。其中,唐朝一面直接继承了隋的成果,一面与隋有着这样那样的渊源,因而,唐人的评价又颇可玩味。
一、影响唐人评价的时代因素
1.政治环境的变化
唐前期,统治基础并不稳固,直到贞观之治时期,地方上仍不时有小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这一时期否定隋炀帝,
既可以从亡国之君的失败中得到启示,以资治道,又可以通过“过隋”塑造唐王朝政权的合理合法性,还可以统一思想,引导舆情。
展开剩余91%于是,大唐创业君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积极吸取隋亡教训,批评隋炀帝的政治污点,以期“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唐中期,随着内部统治基本稳固,外部战争频率显著降低,李唐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此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皇室内部的争斗成为统治者面临的主要矛盾,他们无暇他顾,对隋炀帝的关注因而降低。
唐晚期,政治黑暗,经济萎靡,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李唐面临了全方面的危机。这一时期评价隋炀帝,在朝,则是全面评价隋朝、隋炀帝时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在野,则是通过批评隋炀帝事迹针砭朝政。
唐前期缺少对隋朝制度的评价,相当现实的原因是,唐初承袭隋制,基本的制度框架没有大的变动,而且时间过短,无法对制度发展的潜流形成历史的、总结性的看法。
唐后期对隋炀帝个人文采和文化事业的认可,则反映了此时文风世风的变化,换言之,这是科举制发展,科举出身的文人渐多,文教昌盛的结果。
同时,社会危机到了“穷则变”的时机,内政不修,外敌环伺,要重建一系列适合当下的制度,反思以往的不足,按照封建传统,当然要去史书中寻找答案。
2.经济因素的影响
唐前期,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统治者亟需与民休息,而非对经济社会大幅度变动。因此,制度上,唐朝基本承袭隋朝,对隋炀帝的批评主要落脚在他个人的政治才能和品格上,而非否定隋朝的制度。
唐中期,经济得到恢复,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李唐君臣开始埋头建设,对隋炀帝的盖棺论定已经过去,回顾历史对现实社会的指导价值降低。
唐晚期,随着安史之乱对李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经济重心南移,经济环境出现深刻变化,统治阶级腐化糜烂,承袭自隋的诸多制度不再适应于当下的社会现实。
因此,一方面,反思、批评隋炀帝乃至整个隋朝创立的制度,历史性地总结成为这一时期评价隋炀帝的中心,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对统治者奢侈浪费的行径越发不满,进而回顾历史,将这种不满发泄在批评、丑化隋炀帝的活动中。
3.思想文化的转变
唐前期,经历过自西晋至隋末的长期分裂、动荡,李唐君臣亟需重建统治秩序,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前朝做“清算”。
举例来说,宰相监修国史自唐始,武德贞观以来,唐代编纂了“唐八史”,占廿四史的三分之一,工程之巨,旷古绝今。
换言之,史学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与之相符,唐人也有相当的历史责任感和自觉意识,因此积极观照历史,以古鉴今
。
唐中期,隋炀帝已经成为历史,人们对隋末的情况缺乏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
即便后世帝王怀古,也自有祖宗法度《贞观政要》为资。
并且,唐初君臣年富力强时期多生活在隋朝,隋炀帝对他们来说是近在咫尺的政治人物,他们对隋末的社会情况也是感同身受,这与前期情况大为不同。
唐晚期,随着市井经济的发展,俗文化迅速崛起;政治黑暗,世家大族回光返照,中下层士人怀才不遇,士人与乐府关系越发密切,这两者共同孕育、滋养了唐传奇的盛况。
若干怀才不遇的中下层书生、生计艰难的底层百姓,成为唐传奇的创作者、传播者。思想文化的载体改变、受众改变,对隋炀帝的评价因势利导发生变化。
二、不同群体唐人评价的基本内容和取向
《谥法》说,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则赐之善号以为称也。谥号,就是帝王的盖棺论定,按照封建时代的评价体系,谥号是最能够简洁、直观地反映官方态度的评价。杨广其人,唐室尊谥曰炀。
《谥法》曰: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
与之相对,唐代承认的隋朝最后一个正统皇帝杨侑被谥曰“恭”,盖取其敬有德,让有功之意,情感色彩大为不同。
显然,即使名义上李唐以杨侑(恭帝)为末帝,但炀帝为亡国之君却是共识,此后三百年间,
“炀”奠定了对杨广评价的基本方向,又因为评价时空及主体的不同,各有侧重。
1.朝堂君臣
“君子务本”,朝堂君臣对隋炀帝的关注点,自始至终在政治方面。
唐朝初年,对隋炀帝是全然否定的。就评价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炀帝政治素养及作为方面:
其一,批评炀帝亲佞远贤。其二,批评炀帝穷奢极欲。其三,批评炀帝有才无德。其四,批评炀帝残暴不仁。其五,批评炀帝穷兵黩武。
唐中后期,君臣对隋炀帝的评价基本仍是否定的,但在细节上呈现出差异。
除了仍然批评隋炀帝用人不明、穷兵黩武、残暴不仁等个人政治素养、生活作风的恶劣,突出的变化在于,朝臣、史家对炀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所褒贬,
对他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对隋炀帝个人的文化素养及这一时期的文化制度却是给予了一定认可。
2.中下层读书人
中下层读书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朝堂和市井之间桥梁的作用。中国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士又一向讲求实践理性,怀有经世致用之心,从这个角度似乎很难将官员和读书人割裂,读书人,理想状态下都是“职前官员”。
但是中下层读书人同时更近于市井,与朝政的联系较弱,因此,
一方面,他们有更多时间,更大自由以儒家道德为准绳,评判杨广的功过,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方便做出雅俗共赏的成果,为杨广形象的“大众记忆”添砖加瓦。
在唐前期的历史记载中,第一种人的评价拥有绝对优势数量,君臣之外零星可称为“中下层士人”的论者,有史可考的唯杜宝(撰《大业杂记》以补《隋书》之缺)而已。
唐中期,更多人的评价开始以诗歌形式流传,并首次出现了小说这一新形式,君臣的第一要务仍在论政,怀古诗因而有限地补充了其他群体的视角。
这与诗歌在数十年间地位的变化不无关系,初唐时期,诗词被视为小道(或者说相对于论政,诗词始终是封建社会的小道),到玄宗朝,诗赋入科举,达官显贵追捧诗人。
这促进了不同题材和体裁诗歌的发展,诗,越来越成为士人得心应手用以表达自我、展现思考的文体。天宝前后,针对玄宗皇帝奢靡无度的“借古讽今”型评价已经出现。
唐晚期,如前所说,笔记小说大量出现,诗更是一跃成为评价的主要载体。同时,由于君臣失职,更多中下层官员、读书人起而成为这一时期评价的主要群体。
无论诗歌、小说,讲古的最终目的是鉴今,考虑到中下层读书人的社会身份,他们的主要情感是表达对国家朝政和个人命运的不满。
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停留在了这种不满中,生发出各种诗歌意象,对于现实政治却无力形成多少帮助。
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过错,但令人失望的是,抛开现实政治,与唐初朝野慨然治史的豪气相比,晚唐也无私人著史以评价隋炀帝者,他们的服务群体,似乎已经从飘渺的后世,转变为现实的市井百姓。
这倒也有一点好处,在言为心声、文以载道的天然限制之外,若干以此为业的读书人当然要迎合市场,写出大众认可的作品。
3.市井百姓
市井百姓,在传统中国史学记载中,始终是失声的,大部分百姓无力在历史记载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更不必说传达思想观念。
当后人想要探究他们的想法时,只能求之于“为百姓代言”的小说、小说家。
唐中后期,小说家结合民间轶事和传闻,大量创作出以隋炀帝为中心的笔记小说,
很大程度上是为传统史学中原本失声的百姓代言,反映了百姓对隋炀帝的普遍看法,形成了“作为神话的隋炀帝”。
小说有志人的部分,就是描写隋炀帝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有志怪的部分,就是以神鬼之事论述隋炀帝的亡国之兆。
《隋遗录》写隋炀帝龙舟的布置,说,“舟前为舞台,台上垂蔽日帘,帘即蒲泽国所进,以负山蛟睫幼莲根丝贯小珠间睫编成,虽晓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择妙丽长白女子千人,执雕板缕金楫,号为殿脚女。”
过分细致乃至猎奇的描写不免有失真实,这虽然是中下层文人对前朝昏君生活细节的想象和评价,
若干年后洪昇《长生殿》写七月七日事,也存在这个毛病。
小说《海山记》称,隋炀帝出生时“红光竟天,宫中甚惊,是时牛马皆鸣。帝母先是梦龙出身中,飞高十余里,龙坠地,尾辄断”,这是噩兆。到隋炀帝三岁时,文帝评价称“是儿极贵,恐破吾家。”
这些谶纬式的话语引向一个似乎是命定的结局——隋朝灭亡,炀帝成为亡国之君。有意思的是,对隋文帝,
同一时期的小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具体表现为小说家杜撰种种征兆以证明文帝是真命天子,理应登基。
以封建伦理,反观炀帝相对文帝的这种“不肖”、这种似乎是出自天意的违背,
在当时是不可忍受的污点,或者说,是百姓对隋炀帝最为淳朴而恶毒的诅咒。
唐人对隋扬帝的评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隋炀帝评价的变化,和对“隋炀帝评价”的评价、解释炒股杠杆啥意思,背后都蕴藏着当代的需要。
发布于:天津市